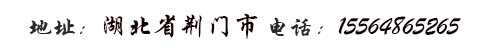中医教你如何开方
|
白癜风哪里可以根治 http://baidianfeng.39.net/bdfcs/zhiliao/ 处方,作为中医理论中理、法、方、药这一严密逻辑体系中的核心环节,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它不仅是医者智慧与经验的结晶,更是连接诊断与治疗之间的桥梁。在深入剖析病因病机,准确把握病情本质之后,治疗策略如明灯般照亮前行之路,而处方的拟定,则是将这盏明灯转化为实际操作的蓝图。辨证,犹如侦探般细致入微地搜集线索,以确定疾病的真相,它是通往治疗方案的必经之路。而拟定处方,则是基于这一真相,精心策划的解决方案,是破局的关键一步。在处方拟定的艺术中,两大流派交相辉映:一是以古为鉴,取法乎上,选取经典古方或成方,依据病情变化灵活加减,犹如匠人雕琢美玉,既保留其神韵,又赋予新貌;二是独辟蹊径,根据病情的独特性,匠心独运,设计出全新的治疗处方,如同画家挥洒自如,绘就一幅幅独一无二的医疗画卷。关于是否应效法古方,学界历来存在争议。有人如冯兆张在《锦囊秘录》中所言,视古方为典范,主张“仿”其精髓;而日本汉方学家更是将这一理念推向极致,他们近乎虔诚地遵循仲景原方,不加改动,直接用于临床,如小柴胡汤、小青龙汤等经典方剂,被精心配制成成药,陈列于药铺之中,供人选用。 但是,在医学领域内,亦不乏有人对古方的运用持反对态度。譬如清代名医陆成一,他强调治病应当深入熟悉各类药物的性质与功效,而不应被固定的成方所束缚。他掷地有声地言道:“方,不过是诸多药物的组合排列罢了,为何说用药可,用方却不可呢?实则,每一种药物都有其独特的性质与功效……唯有深刻洞察药性,方能自如地遣方用药。”而吴鞠通更是直抒胸臆,提出了“拘方治病,病必危殆”的鲜明观点。他比喻道:“学医如同学弈,医书犹若棋谱……然而在对弈之时,若一味照搬棋谱以应敌,那便如同胶柱鼓瑟,注定会一败涂地。医术又怎能例外?以固定的成方去治疗千变万化的病症,强行将病症套入方中,这如何能承受得起人命的重托呢?故而先贤有云:检谱对弈弈必败,拘方治病病必殆’。”(语出《存存斋医书稿》)吴鞠通虽反对生硬地套用古方,但在其《温病条辨》中,却也巧妙地融入了一些经典方剂。其实,他真正反对的是不加变通地照搬古方,而非全然否定古方。我认为,仿古方治病与依据病情独立制方,二者相辅相成,缺一不可。我在临床实践中,尤为重视采用那些历经岁月考验的经方名方,但绝非刻板模仿,而是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与体质,灵活地进行加减化裁,力求精准施治。古方名方,往往结构严谨,药物配伍更是历经千锤百炼。它们之所以被称为经方或名方,是因为它们经过了漫长历史的检验,且广受认可。因此,我认为采用古方名方进行加减治疗,不仅疗效显著,更是明智的选择。然而,如何巧妙地运用这些古方名方,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。我们主张借鉴古方名方,但绝非生搬硬套。因为成方虽多,却难以涵盖临床上的万千变化。面对每一个独特的患者,都有其特定的病情与体质。故而,即便是选择了某一成方,也需依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变通。通常有以下几种处理方法。1.在原方的基础上药物加减,或者在结构上调整举例而言,众所周知,《伤寒论》中的麻杏石甘汤,犹如一剂古老的智慧之钥,常被寄予厚望于小儿肺炎的治疗之门。然而,临床实践的熔炉中,却屡屡揭示出一个不容忽视的真相:若原封不动地套用此方,而不依据病情灵活加减,其疗效往往如同夜空中微弱的星光,难以照亮患儿康复的道路。细细审视,《伤寒论》中麻杏石甘汤所治之证与小儿肺炎的临床表现,虽同有发热气喘之表象,但实则差异微妙而关键。前者乃伤寒之后,余热留恋,如顽童嬉戏于肺金之地,身无大热而汗出喘息;后者则属温病范畴,温热之邪如烈焰熊熊,夹毒而行,故需强化清热解毒之力,犹如夏日暴雨,骤然而至,以熄其焰。再者,小儿肺炎之喘憋,犹如狂风骤起,肺气上逆,亟需降气平逆之药,如苏子、葶苈子,犹如舵手稳舵,平息风浪。于是,我在运用麻杏石甘汤时,常于原方生石膏之外,添黄芩、知母,犹如炎炎夏日中的清风,加强清热之力;金银花、连翘如两朵解毒之花,绽放于方中,以解其毒;苏子、葶苈子则如两员大将,镇守肺气,降逆平喘。如此加减,疗效自是如虎添翼,显著提升。同样,《伤寒论》中的白虎汤,乃清泄气分热之利器,广泛应用于外感热病的治疗。然而,其应用亦需审慎,如吴鞠通于《温病条辨》中所言,白虎汤之禁忌,犹如四把利剑,悬于医者心头。脉浮弦而细者,脉沉者,不渴者,汗不出者,皆非其宜。然而,医者需知,伤寒温病,白虎汤皆为热病治疗之重器,不可因禁忌而束之高阁。如俞根初于《通俗伤寒论》中所创新方,便是灵活运用白虎汤之典范。2.多功能成方,要根据不同的应用目的,做不同配伍如甘桔汤,这剂古朴而精妙的方剂,其构成虽简约至极,仅桔梗与甘草两味药材携手,却蕴含着利咽、排痰、排脓三重神奇功效,宛如大自然赋予的灵动乐章。若欲借其利咽之力,则需巧妙融入牛蒡子之清润、黄芩之苦寒、金银花与板蓝根之清热解毒、玄参与麦冬之滋阴润燥,众药合力,共筑咽喉之坚固防线。若旨在排痰,则需陈皮、半夏之辛温化痰,茯苓之健脾利湿,瓜蒌之宽胸散结,四药并用,如春风化雨,痰浊自消。至于治疗肺痈,意在排脓之时,甘桔汤则需与千金苇茎汤并肩作战,更添鱼腥草之清热解毒、败酱草之破瘀排脓,犹如利剑出鞘,直捣黄龙,脓毒无所遁形。再如二陈汤,化痰之名方,然痰之种类繁多,有寒、热、燥、湿、风、顽之别,犹如世间百态,各具特色。故治痰之时,二陈汤亦需灵活变通,随证加减。化热痰,则黄芩、瓜蒌、竹沥水、浙贝母、冬瓜仁等清热化痰之品纷至沓来;化寒痰,则干姜、细辛乃至附子等温阳散寒之药温暖如春;化湿痰,则厚朴、苍术等健脾燥湿之材如清风拂面;燥痰则知母、川贝、麦冬、天花粉、百部、百合等滋阴润肺之物如甘霖降世;风痰则天麻、胆南星、白附子、僵蚕等祛风化痰之药如狂风扫落叶;至于顽痰,则需枳实、礞石、大黄等峻猛之药,如雷霆万钧,顽痰自散。3.在临证施治的过程中,针对病情的多样性与复杂性,我们往往需要采取灵活多变的策略,将两方或多方巧妙并用,以期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。面对那些病情错综复杂的病例,单一成方往往显得力不从心,难以全面覆盖病机的各个层面,这时,多个成方的协同应用便显得尤为重要。譬如,在治疗一位顽固性呃逆的患者时,我细致辨析其病因病机,发现乃是由肝郁气滞、痰饮内阻所致。于是,我果断采用柴胡疏肝散以疏肝解郁,小半夏加茯苓汤化痰饮、降逆气,旋覆代赭汤和胃降逆,三方合力,共奏疏肝化痰、和胃降逆之效,最终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疗效。又如,在治疗腹泻的病症时,我依据湿热泻、伤食泻、脾虚泻等不同证型,分别采用不同的成方组合。对于湿热泻,我常用葛根芩连汤清热燥湿,配以四苓散分利止泻,二者相辅相成,共除湿热之邪;对于伤食泻之久泻,我则采用保和丸消食导滞,结合四神丸固涩止泻,标本同治,止泻效果显著;而对于脾虚泻之久泻,我则选用参苓白术散健脾益胃,与四神丸合用,涩肠止泻,共复脾胃之健运,止泻而固本。4.从古方中提取经典配伍,在古方名方之中,有许多精妙的配伍,在长期应用中,被人们看作是经典的配伍。我们将这些经典配伍,从古方中提取出来,应用到各种场合的处方重组中去,以制定相应的新方。举例来说,麻黄、杏仁的配伍是一组很好的宣肺止嗽的配伍,它来源于《伤寒论》的麻杏石甘汤。这一组合再经过不同的配伍,可以广泛地应用于各种咳喘证。《伤寒论》中有五个泻心汤,用以治疗痞证。这五个泻心汤中,除大黄黄连泻心汤以外,其余四个泻心汤,都有黄芩、黄连、半夏,这是一种精妙的辛开苦降的配伍。我常将这一配伍,广泛地应用于脾胃病中有痞满症状者,收到良好效果。《伤寒论》的茵陈蒿中茵陈蒿配栀子,是消退湿热阳黄的经典配伍,为治疗黄疸所常用。《丹溪心法》中的二妙丸,乃苍术、黄柏相配伍,这是清热燥湿的经典配伍,是治疗湿热证的良方;后来《医学心悟》在二妙丸中加入牛膝,变成了三妙散,更善于治疗下焦湿热,是治;薏苡仁,进一步加强了清利下焦湿热的作用。我们在学习方剂学的时候,用心汲取这种经典配伍,对我们制方有极大帮助。5.为了突出某一方面效果,需要在成方基础上强化用药许多成方名方,是我们制方的典范。但是这些成方名方,仍然存在修改变化乃至强化的空间。有时候我们选择了某一个成方,为了提高某一方面的治疗效果,可以加入某些同类药物,以强化某一方面的效果。例如遇到肾阴不足的病人,我们可以选择钱乙的六味地黄丸,为了加强滋补肾阴的作用,可以加入女贞子、枸杞子、金樱子乃至龟甲、阿胶等;遇到肾阳不足的病人,我们可以选择《金匮》肾气丸,为了强化温补肾阳的功用,可以加入补骨脂、菟丝子、巴戟天,乃至鹿茸等补阳药。6.了解名方的沿革,汲取其中思路演变,来改进临证制方技巧,随着中医学的不断发展,一些成方的制方思想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,变得更为严谨,更为准确,更加全面,从而其疗效也随之进一步提高。例如,外感病解表方的制方思想的演变,从单一的辛温解表解膀胱经之邪,发展到辛凉解肺经之邪,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——首先始于《伤寒论》的辛温解表,采用单一辛温发汗的麻、桂二方。第二阶段是宋代钱乙的《小儿药证直诀》制定了人参败毒散,后来明代《摄生众妙方》又将上方去人参加荆、防,改名为荆防败毒散。这是以荆、防、羌、独等辛温解表药代替了昔时的麻、桂,使辛温解表(解太阳经之邪)前进了一步,实现多元化。第三阶段是宋代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制定的凉膈散,已经显现了从解膀胱经之邪向。解手太阴肺经之邪的过渡。第四阶段是金元时代李东垣制定了清心凉膈散(黄芩、栀子、连翘、薄荷、桔梗、竹叶、甘草),已经鲜明地突出辛凉解肺经之邪,清肺经之热。最后到了清代,叶天士提出“温邪上受,首先犯肺,逆传心包”的著名论断,吴鞠通在此基础上,完成了专门用于温病辛凉解表的桑菊饮、银翘散的制定。至此,结束了历史上寒温不分的错误,建立了辛温辛凉同时并存的局面,使外感病解表法走上正确的道路。在了解了解表的发展过程及发展脉络后,我们在临床上治疗外感病的时候,就能够更好地运用解表法,使之针对性更强。例如我将辛温解表分成两种,即风寒外感而以肺闭咳喘为主要表现的时候,采用麻黄类方加减治疗;如果风寒外束,表气郁闭,导致发热恶寒、身痛无汗时,则采用羌活、防风等药剂,即以荆防败毒散为主来辛温发汗解表。实践证明,辛温发汗解除表郁,羌防胜过麻桂;而散寒定喘,则以麻黄类方为胜。辛凉解表,取银翘散中荆芥穗、薄荷、金银花、连翘以辛凉清透,多数情况下,考虑到当今小儿,内热多盛,多需加黄芩、板蓝根或生石膏等以清肺胃之热。又关于少阳膜原理论的发展,加深了对半表半里证的理解,改进与丰富了对半表半里证的治疗方法。半表半里涉及少阳和膜原。膜原理论早在《黄帝内经》就已经被提出:“其间日发者,由邪气内薄于五脏,横连膜原也。”这条记载,语言虽然简单,但是对于膜原的位置,它与脏腑的关系,以及它与疟疾发作的关系等方面,已经有清楚的描述。暗示膜原地处脏腑之外,显然又非在皮毛,是为半表半里;又疟疾之休与作,乃疟邪出入于膜原与脏腑之间。对于这样一条重要记载,长期没有引起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dannanxinga.com/dnxcd/13786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让新质生产力在朝阳形成生动实践北京市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