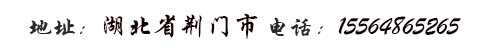中医科普痰饮水湿
|
北京看白癜风病的医院 http://baidianfeng.39.net/水湿痰饮,四者虽同为津液代谢障碍之病理产物,但其间之差异却不可忽视。治疗时,虽整体原则遵循仲景的“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”,然而具体之方剂选择却需因病而异。痰湿因其重浊之性,治疗当以行气、化痰、化湿为主,如二陈汤之运用,能有效疏通气机,化解痰湿之困。而水饮则相对清稀,治法当采用淡渗之法,如五苓散之类,旨在引导水湿从体内排出。苓桂术甘汤为代表的苓桂剂,其功效在于温阳化饮,对于水饮之病颇为适宜。若误用以治疗痰湿,则恐难收良效。痰湿水饮,皆属有形之邪气,其性质缠绵,病程漫长,易阻气机,易犯脾胃,易伤阳气。因此,在治疗痰湿时,仍需辅以行气之法,以助化痰、祛湿之功。谈及痰饮水的生成,其根源可追溯到太阴病的影响。在中医后世的理解中,肺脾肾三焦功能的失调,其实质多指向脾的运化功能失健。因此,调理脾的功能,尤其是温运太阴,显得尤为重要。这也正是仲景所强调的,对于痰饮之病,当以温药调和,这不仅是一种治疗方法,同时也揭示了痰饮水湿的本质属性——阴邪。在化痰湿的方剂中,二陈汤堪称经典。若患者伴有气虚症状,则需结合四君子汤,进而形成六君子汤。苓术则以其淡渗之力,成为祛除水饮的良方。若阳气不足,可辅以桂枝甘草,即苓桂术甘汤;若再加入附子生姜,则成为真武汤。当然,苓术本身亦具备化痰化湿的功效,只需适当配伍,如在二陈汤中加入茯苓,或在藿香正气散中运用苓术,皆能取得良好效果。化痰与祛湿虽然有一定关联,但在具体用药上仍有差异。化痰方面,以陈皮、半夏为主的二陈汤为代表,辅以胆南星、瓜蒌、贝母等药物,或三子养亲汤中的紫苏子、白芥子、莱菔子,都能成为攻逐邪气的得力助手。相较于湿邪,痰邪相对有形,其行气力度更大,容易引发气机阻滞、痰气互结的情况。因此,在方剂如二陈汤、半夏厚朴汤、温胆汤中,都少不了陈皮、半夏的辛开之力,以助行气化痰。 湿邪相对弥漫而无定体,温病学派对湿邪论述的更为精详一些,三仁汤、藿朴夏苓汤都是著名方剂。当然温病的方更多是治疗湿热的。比如湿重热轻的三仁汤、湿热并重的连朴饮、热重湿轻的白虎加苍术汤。湿邪本身属于阴邪,但郁久容易化热,湿热相合难解难分,所以要分消走泄,在整个痰饮水湿当中治疗难度是最大的。 水饮之病,犹如江河之水泛滥成灾,需得用淡渗之法,方能引导其回归正道。水饮之病,多属阴证,因其清稀之性,温性药物便显得尤为重要。诸如苓桂术甘汤、五苓散、真武汤等方剂,皆为温阳利水之佳品,用以驱散阴霾,恢复水液之正常运行。然而,水饮之病亦有化热之变,此时则需用寒凉之药以清热利湿。如猪苓汤,便是一剂清热利水的良方,它能将体内的湿热之邪一扫而空,恢复身体的清爽与和谐。治疗痰饮水湿之病,犹如排兵布阵,需得遵循一定的规律。行气之陈皮半夏,能疏通气机,化痰止咳;健脾之白术茯苓,则能培土制水,杜绝生痰之源;芳香之藿香佩兰,可化湿醒脾,令人神清气爽;畅运气机之厚朴腹皮,则能宽中理气,消除胀满之感;淡渗利水之猪苓泽泻,则能将体内多余之水湿排出体外;攻逐之三子养亲汤,更是峻猛之剂,能迅速攻逐体内的痰饮。化痰之药,如贝母、瓜蒌、南星、竹茹等,皆能化痰止咳,令人呼吸通畅。二陈汤、温胆汤,则可作为化痰之代表方剂,它们能调和气机,化痰止咳,令人倍感舒适。对于湿邪之病,藿香正气散和芳香化浊法可说是治疗之良策。它们能芳香化湿,醒脾开胃,令人体内的湿邪得以消散。而对于化热之湿热病,三仁汤、连朴饮等方剂则能清热利湿,令人体内的湿热之邪得以清除。综上所述,对于水饮之病,采用苓桂术甘汤、五苓散、真武汤等方剂,可温阳利水,恢复身体的和谐与平衡。而对于痰饮水湿之病,则需遵循一定的规律,选用适当的药物和方剂,方能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。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dannanxinga.com/dnxgx/13000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中药橘皮的使用方法看这篇就够了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