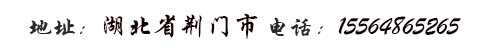干咳痰咳令人纠结的咳嗽
|
(图片来自网络,侵删) 本案其实算是半个误案,幸而后面扭转了回来,因有成功之“令堂”在其中,似也更有价值,故记录下来。 患儿,男,四岁,因近日多吃零食,引致咳嗽,咳声乍听像是干咳,细听又似有痰,日轻夜重,有时半夜醒来更见严重。近段时间手脚常长小水泡,颇为困扰。 一诊,年11月12日。脉象略浮数,不渴,基本每天都有大便,但常感排便难,舌尖红,舌苔中部及舌根干腻。这种情况,当为脾胃较为虚弱,既有痰湿,又因津液不足产生虚热,湿热纠结,故而手脚作痒;热重于湿,痰湿为之蒸凝,因此咳声近于干咳又似有痰。此前该患儿咳嗽,多以麻杏甘石汤对治而获显效,本次虽有较明显痰湿,但热更重于湿,故而仍疏麻杏甘石汤方与之,另加法半夏、陈皮,2剂。 (图片来自网络,侵删) 二诊,11月14日。上方服毕,咳嗽不见好转,也未加重,湿痒依旧。脉象还是偏浮数,只是较之前稍微沉伏一些。舌尖热象犹在,舌苔更为厚腻,且上面明显有一层水迹。考虑到此前已用了两剂麻杏甘石汤加味清热,腻苔由干转湿,而咳嗽症状却未明显改善,宜健脾祛湿兼以清热,转予苓桂朮甘汤加石膏、干姜、半夏,干姜只用了1克的量,重用生白术、石膏,健脾与清热同用。不想当晚咳嗽明显加重。此时我犹认为这是应有的反应,因以前治咳,有时虽然用对了药,但因湿痰外出引致咳嗽加剧,也属正常。11月15日,让其继续服用上方,只减去较为燥热的干姜。 当夜,咳嗽更重,几乎是躺下便咳,几无安时。至此,我方惊觉用药方向错了。虽然患儿咳嗽痰声明显,但咳声沉闷,显见为黏稠之痰,此时急用石膏之类清热药化痰犹恐不及,转用桂、朮之类的温热药,只会使其内热更甚,痰更黏稠,更难祛除。前者服用麻杏甘石汤加味虽未好转,也未加重,已说明本方对证,只是药轻病重,故而看似无效。须知《伤寒论》诸方较之后世方,多数偏性更为明显,如能辩证对治,自然效如桴鼓;但若错服,其反扑之力也颇惊人。因此往往服药之后病情没有加重,即说明辩证无差,只是方剂结构、药物剂量不甚切合而已。 三诊,11月16日,转予麻杏甘石汤加法半夏、胆南星、陈皮、大黄,重用石膏、半夏、胆星,取石膏清热之力,期能化痰为水,再由半夏、胆星等化痰药将痰导出;又因其常有大便难的问题,另加大黄1克,与诸药同下,取其清热之力,兼有少许通便之功。恐石膏清热化痰之力不足,又让其同时服用复方竹沥口服液(本想让其服鲜竹沥,但本地药店无售)。如此连服4剂,至11月18日,咳嗽基本痊愈,湿痒减轻,让其继服参苓白朮散善后。 本案辩证之难,在于该患儿的咳嗽看似痰咳,实则热甚于湿,一般的温肺化饮或清热祛痰都不可行。其中最难便在于寒热药比例的把握,既要清热化其黏痰,又要有足够的祛痰药将痰排出,缺一不可。 犹记得我学医之初,某中医名家讲述用《伤寒》方治咳,举其大略而言,将咳嗽分为痰咳、干咳,痰咳用小青龙汤,干咳用麻杏甘石汤(当然,他也讲到了如果痰较黏稠,可用小青龙加石膏汤。但他似乎是将此方作为小青龙汤的加味来讲,未予足够的重视)。如此分类,对于初学者理解方剂当有不小的帮助,但实践中却远非如此。事实上,纯粹的痰咳或干咳并不多见,痰咳夹热或干咳夹痰则更为常见。而因现代人多贪凉喜冷,因此痰咳夹热的情况又远多于干咳夹痰。另外相比较而言,成人多见痰咳夹热,小儿则常有干咳夹痰,这也是因为孩童年纪尚小,其先后天之气还未遭受太大破坏之故。因此治疗咳嗽时,凡因外感而起者,我多选用小青龙加石膏汤加减进行治疗,再视其转归选用苓桂朮甘汤、理中汤、附子汤、真武汤乃至肾气汤之类加减味进行善后。对于干咳的咳嗽,我常用麻杏甘石汤加减对治,此前也多取得不错的疗效,但总觉得收功不甚得力。 从此案来看,不论痰咳、干咳,其实质都因脾胃虚弱,运化无力,致使痰湿滞留体内。痰湿生,则阻滞津液运行;痰湿多,则相应的津液虚少。如果其人久虚久寒,多表现为痰饮咳嗽;如其人气血尚足,则因津液偏虚阳热有余,表现为干咳。因此或可以说,不拘痰咳干咳,其实质都有痰饮存在,只是痰咳以痰为主,干咳以热为主。所以,即使是治疗偏于干咳的情况,也需要在清热之余酌加化痰之品。如热多痰也多,则清热药、化痰药都应加量,方能奏效。 (请长按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dannanxinga.com/dnxdx/9888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膻中穴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