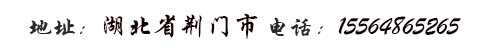揭秘ldquo博物君rdquo微
|
博物少年、昆虫学硕士、《博物》杂志编辑、博物君——这是北京小伙儿张辰亮一路的成长路径,同步成长的还有从2万到万的粉丝数,以及博物学在中国的热度 “博物君,这是什么蛇?有毒吗?”照片里是盘作一团的褐色条状物,评论里一堆惊恐的吱哇乱叫——博物君答:“绳子。” 有人炫耀养的杂毛小鸟,说是雏鹰,网友争相揣测什么珍稀品种、值多少钱——博物君答:“鹌鹑。” 一只灰色大鸟在防盗窗上筑巢,“博物君,这是什么鸟?我该怎么做?”——博物君答:“珠颈斑鸠,爱在人类窗台上孵蛋。你什么都不用做,趁它外出时把那半倒不倒的花盆扶正了就行,我看着难受。” 每天,博物杂志的微博右上角都会跳出五千多个新 。千奇百怪的动植物照片,“来不及拍照”的手画生物,还有“梦里见过的怪兽”,地摊里的真假古董,匾额上的甲骨文……几千个滴滴叫着,叽叽喳喳嗷嗷待哺地等博物君一一投喂。知乎有个讨论:“博物君为什么什么都知道?”有言之凿凿的回答:“因为博物君不止一个人,背后有一整个办公室。”其实,博物君只有一个人,年出生的北京男孩张辰亮。迄今,博物杂志官方微博已有万粉丝,而年他刚开始管理微博时,这个数字是2万。 叛逃的昆虫学硕士 年,张辰亮有两个身份。 他是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分类学研究生,专门研究一种学名猎蝽、民间叫“臭屁虫”的生物;课外,他是《博物》杂志实习生,专门打理杂志官方微博,昵称“博物君”。 “还是个小孩”就接管“代表杂志形象”的微博,博物君张辰亮发每一条都如履薄冰,“稳妥为主,说话客气,就跟淘宝店亲啊亲的差不多。”那时博物杂志月发行量5万册,微博有2万粉丝,主要用来发杂志节选和新刊预告,有网友不时拍照提问,只是杂志社没有专人解答。 最初,博物君的风格是“卖萌”。讲解认真,“这是双翅目的食虫虻,昆虫界的顶级杀手”。科普一本正经,讲拟态虫子:“大自然的神奇令我们几乎无法用语言形容。”不时卖个萌,“元宵是摇出来滴,汤圆是包出来滴”,后面跟个波浪符。 他发自己养的昆虫照片,从网上搜罗一些生物趣图,间或“答网友问”。几乎没有什么生物能难到他,因为网友提问“九成是科普圈说烂了的常见物种”,只有少部分需要检索。动物分类的类群排列有固定顺序,顺着工具书一检索,很快就知道答案,“普通人觉得我博学,但在圈里我的知识面只是正常。” 张辰亮“特别特别小的时候”就喜欢虫子。他记不清自己养过多少种动物,“看见什么养什么,地上地下水里的,还抓蜥蜴、蛇和鱼。”家里鱼缸和玻璃盒被改造成生态箱,养着甲壳镶黄边的日本真龙虱、蜈蚣和蝎子,也有普通的瓢虫和蛐蛐。他爱观察蝴蝶从虫卵变成蛹,最后破蛹而出,“很短一个周期就能了解它的生活史,比看书管用。” 那时,国内没有太多供小孩看的博物书。学术书配着印刷粗糙的黑白图案,动植物译名不统一,“全是错”,而文字“鉴定方法也看不懂”。学会上网后,张辰亮在昆虫摄影论坛认识了一群网友,有《博物》杂志编辑、也有专门学昆虫的大学生。他还买了大学昆虫学教材,“慢慢就一点点知道了昆虫分类”。在北京五中念高二,他被《博物》杂志选为“博物少年”,那篇报道里写他“可真胆大,什么都敢捉”。 “博物少年”长大后,念了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硕士,搞起昆虫学研究。可他发现,研究昆虫远没有想象的有意思,“一般就是写论文、读博、留学、进研究所,在一个点上越来越专”。 而他喜欢的传统分类学也渐渐式微。研究者们不再像以前那样,一手放大镜一手标本,依据甲壳花纹和触角口器形状为昆虫分类,而是“一堆仪器”取而代之。现在流行分子分类学,“从一个昆虫上扯条腿下来,弄碎,整一堆仪器,搞DNA分析。外形特像的虫子,分析出来关系特远,现在认为这是最精准的。”但是,这套科学工序跟昆虫本身已经不沾边。 传统分类学还有被边缘化迹象,只有研究分子分类法的论文才有机会发到影响力大的期刊。“有这些指标,一下子搞得没意思了。玩昆虫本来是个爱好,后来当事业。不能因为事业枯燥,爱好也毁了。” 他决定从科研转向科普,能继续玩虫子,还能跟别人“分享”玩虫子的乐趣,“自己获得知识很兴奋,告诉别人还能再兴奋一次”。于是他去科普杂志《博物》实习,当起了“博物君”。 卖了一段时间萌,张辰亮不耐烦了,天真可爱的答题语气让网友对博物君的智商将信将疑,觉得是个没经验的小孩,“总问真的假的啊,再加上“不是我本来的性格,自己也觉得挺恶心的”,他开始认真考虑“博物君”的风格。总发自己养的动物不是长远之计;讲解生物趣图的微博号已有不少,没个性。他发现,“回答问题最能展现《博物》特点,最能成为网友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dannanxinga.com/dnxcd/7534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决战便利店之巅关东煮里那么多食材,到底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